安妮的丝巾

坏天气没完没了,五分钟之前是狂风和冷雨,五分钟之后天就晴了,片刻间,乌云又袭卷而来,如此周而复始,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气象预报说明天天气不佳,将有狂风登陆,准确的说,是旅馆的夜班前台说的,我问她是否能报名明天的黄金圈一日游。
她语气坚定地回答:“噢,所有的团都取消了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老天爷。”
还会有比今天更大的风吗?我的内心倒是期待了起来,一个猎奇的旅行者总想要碰上点稀罕事。


可是到了夜晚,天空反而逐渐澄净了,冷冷的月光铺在蓝色的天空底下,街道像在傍晚一样明亮,只是比白天更冷清,店铺的外墙上绘满了攀爬向上的藤蔓和图饰,对面的屋顶下,一只飞舞的老鹰正在墙壁上着陆。
我在街上晃了一圈,像个偷窥狂一样朝每间还在营业的酒吧里张望,这里的年轻人的夜生活居然是在酒吧里喝啤酒玩猜谜游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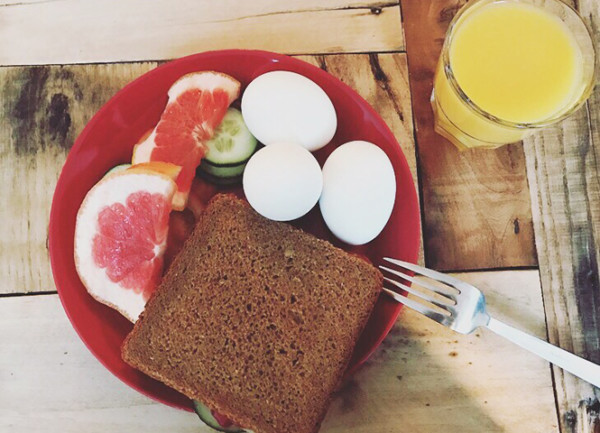

我对吃什么东西毫不在意,而这里的餐厅的菜单上还提供着来自中世纪的料理,鲸鱼肉、鳕鱼舌、海鹦和黑麦面包,我饿了,就点了一份鱼汤和面包,在面包上抹上黄油,裹着温热的鱼汤下肚。天冷的时候喝点热汤,心里就会喜滋滋的。
有个说法是,冰岛人之所以开发旅游业,是因为他们已经无聊到发疯。在这座人口仅有32万的孤岛上,每个人都直接或者间接地认识另外一个人,每个人都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阿姨,表哥,表妹。等你看惯了彼此的模样,看见陌生人的面孔反而会感到很高兴。
我觉得自己在世界的尽头,悄无声息地和这里的人们一起浮于北冰洋之上,在喜怒无常的老天爷的眼皮底下坐在温暖的餐厅里喝鱼汤,有一种无论如何都要愉快地活下去的感觉。
站在狂风中的院子里烧烤,在冷雨里逛街,这样的气候不会令每一个人都感到欢乐,在这个凛冽的岛屿上,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是如此之少,以至于不太相信自己是真正在活着,报纸上写着,有11%左右的冰岛人正深陷忧郁之中。


我认识了新室友,一个夏威夷人,约莫五十几岁,皮肤晒成了棕色,曾经在巴拿马住过十年,她说我的姓氏在夏威夷土语里是水的意思。
我问她:“为什么离开巴拿马?”
“丈夫死了,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了,然后周游世界。”
我的反应颇为迟缓,当别人以这种浓缩的语调讲述人生过往的悲喜的时候,我总不知道该如何作答。不过,她头发的样式以及她的衣着,使她看上去一点也不沮丧,话语温和,没有紧绷的语调。我见过很多人,在经历了挫折和变故之后都变得颇为极端。
她很会闲聊,起初,我们谈了点旅行路线的问题,她说自己已经去过很多地方。很快,话题便转移到夏威夷风光上了。
关于今夜的天气的问题,我们起了一点争论,前台说过,明日有狂风,我认为冰岛的气候变化无常,此刻的晴朗并不代表五分钟之后的晴朗。而这个夏威夷人坚定地认为,只要出现了星星,夜空便会逐渐明朗。
果然,到了深夜,原有的几片乌云也渐渐消散,深蓝色的天空衬得屋顶像雕塑一般。

我说:“安妮,你是对的。”
她眨眨眼睛回答:“只在某些时候。”
然后又补充了一句:“任何人都是对的,只在某些时候。”
有人说,只要是在一个晴朗的夜晚,在夜晚的十一点之后到凌晨的一点之间,即便站在市区楼顶的天台上也能看见极光,我对这种说法不太相信,看极光最好是在没有光源污染的地方。
这个夏威夷人听了却很高兴,过了十一点,她就叫我一起去天台。
旅馆楼上有一个木板搭建的天台,我们等了半个小时,左右张望,天气是零下九度,冻得人瑟瑟发抖,极光当然没有出现,我觉得我们两个是雷克雅未克市最傻气的人,在地球上最北的首都的楼顶上等着月亮给我们投掷礼物。
我说:“我看吧,今夜的极光是不会来了。”
她却指着远处的天际线说:”你看那个是不是?“
那当然也不是,那只是一道白雾。她可能比我还要更轻信他人的无心之言,这个夏威夷人身上仍然有某种天真,是她逐渐衰老的外表所掩盖不了的。
又过了十几分钟,她才相信今夜的极光不会来了。在回去的路上,我注意到了一件事,天气很冷,她的脖子上只系了一条凉薄的绣花丝巾,
我说:“安妮,你是不是应该换一条丝巾?”
这是我见过她反应最激动的一次,她伸手把脖子上的丝巾又系了系,说:“你知道吗?我卖了几乎所有的东西,不过,这条丝巾是个礼物,我戴了它很多年了,是我最喜欢的礼物。”
我便不再做声,我知道有些东西,对于人来说就如同不断回响的钟声。而我们还会不断地前进,去抵达原来不可见,不可听的的另一个世界。
这是看多几本禅书也不会得到的领悟,它可以很复杂,也可以很简单,或许只是因为你有一条熟悉的丝巾,而你还想再戴着它去看看世界。
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微信公众账号:“寻找旅行家”,每天为你精选一篇有见地的独家专栏文章,欢迎关注,互动有奖^_^

上一篇:当一个冰岛的浪荡游民
下一篇:孤独小旅馆之歌








